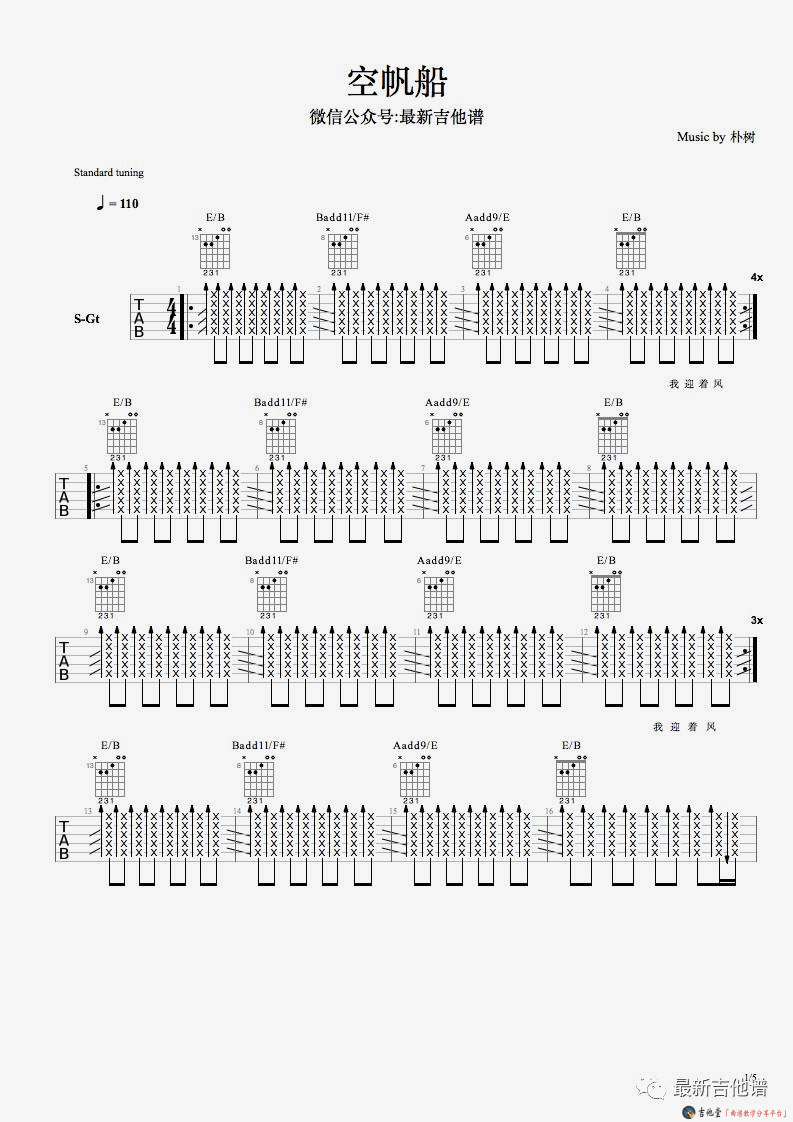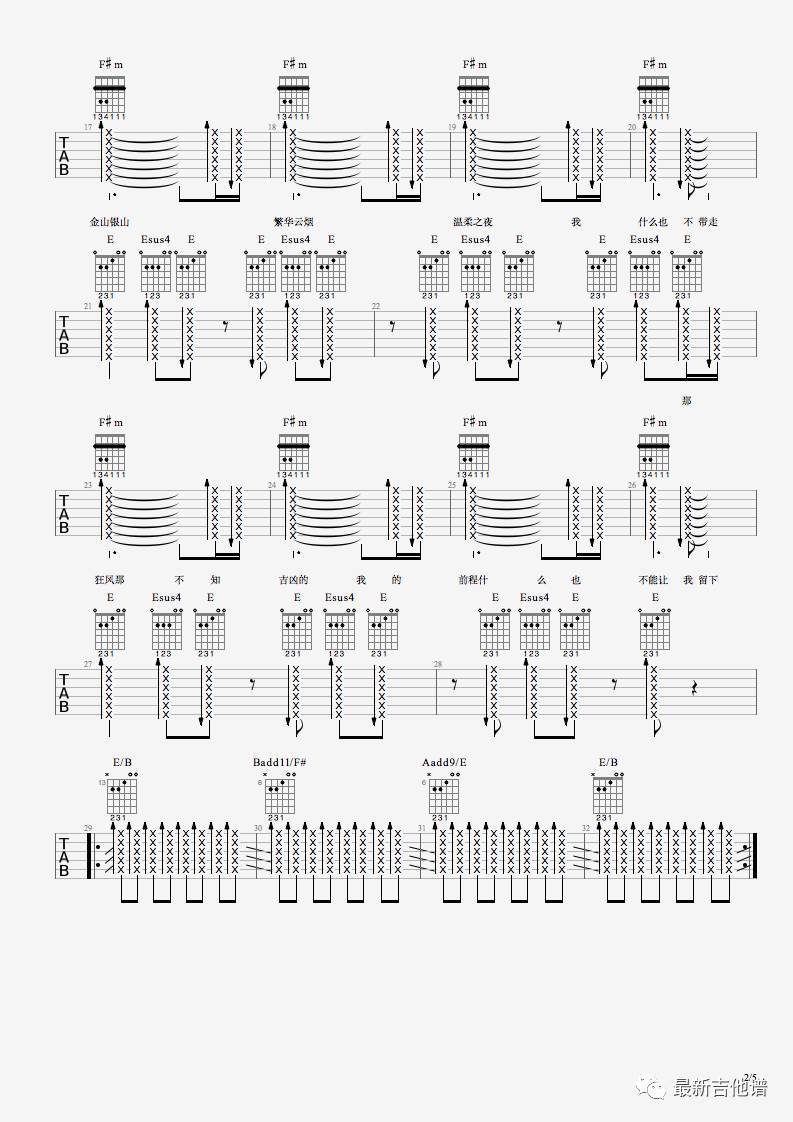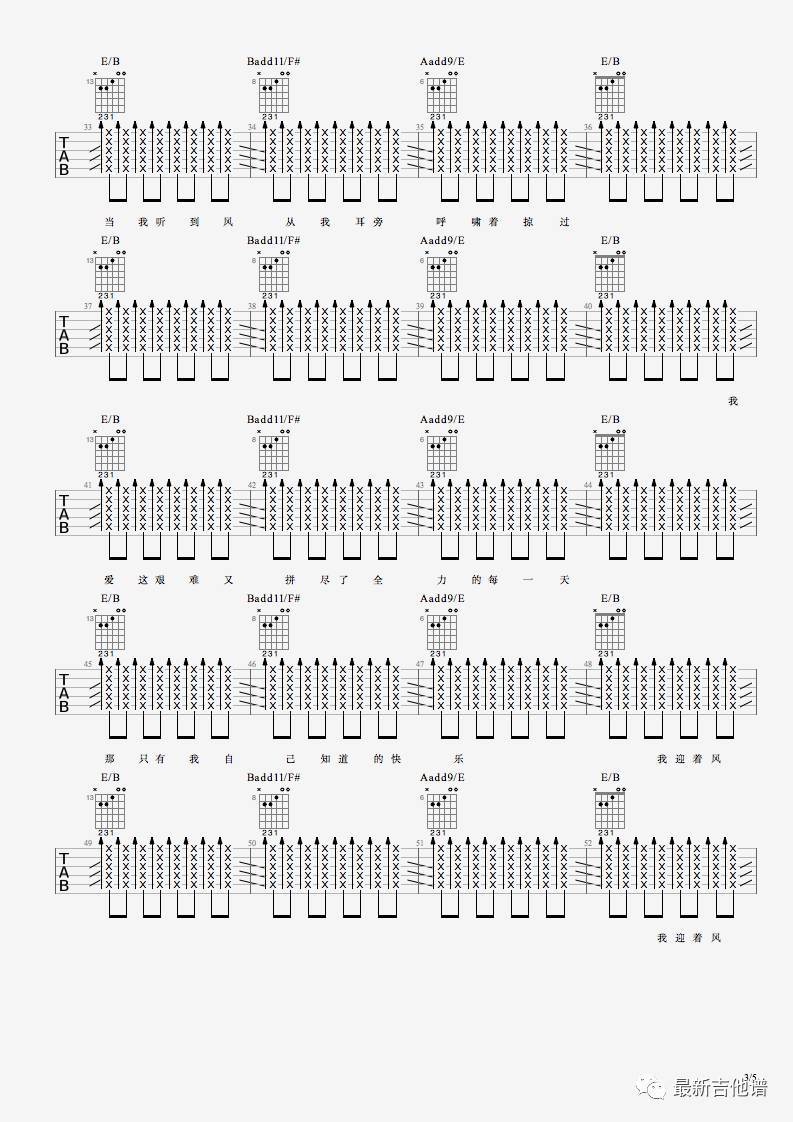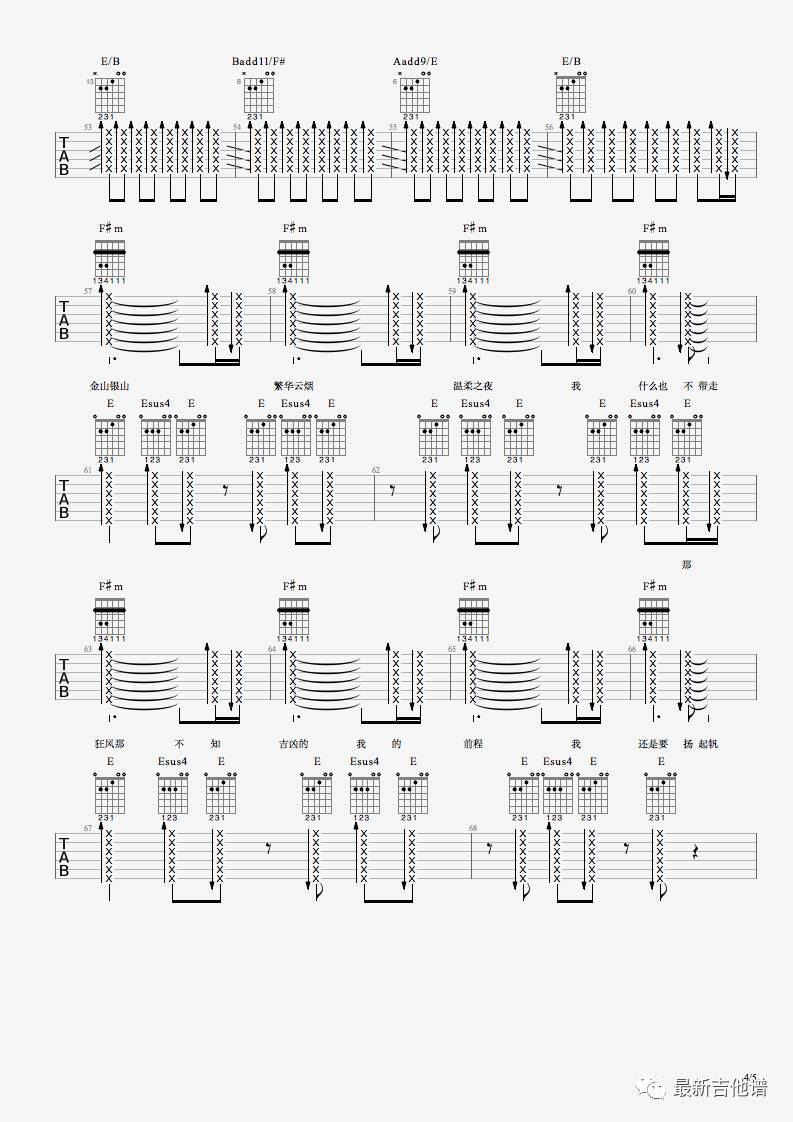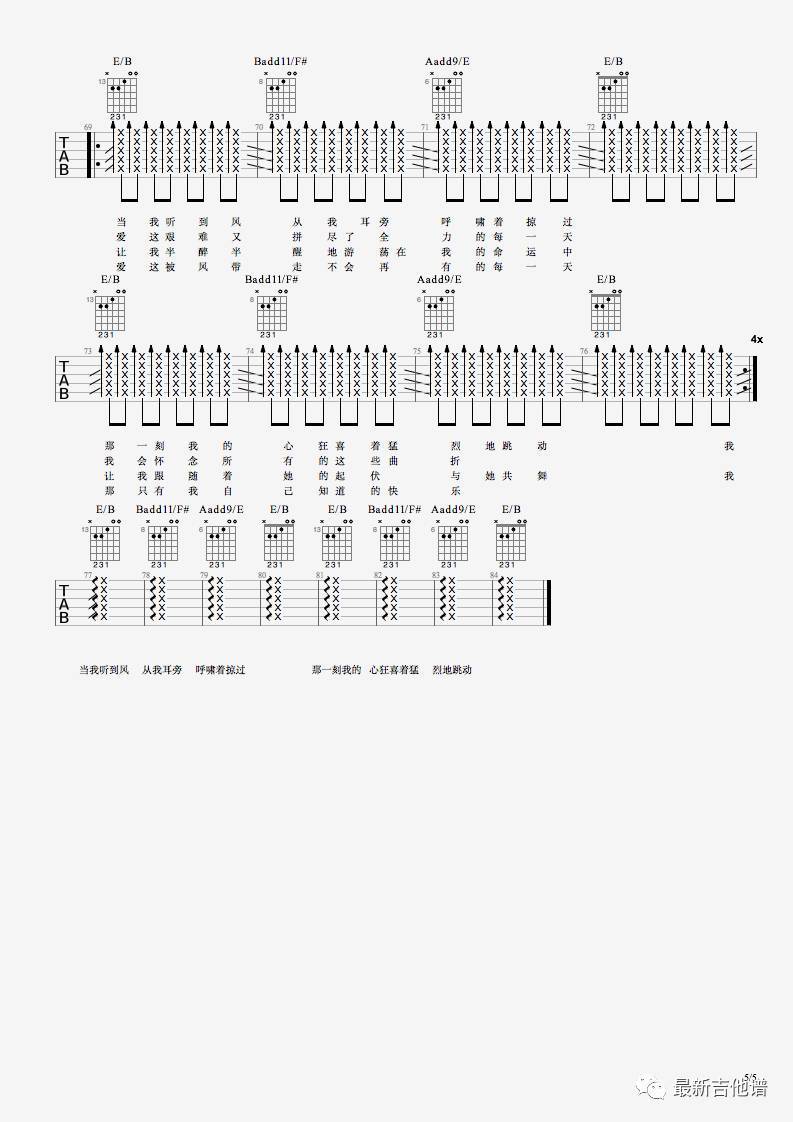《空城》以意象化的笔触勾勒出一座被抽离生命力的城市空间,通过具象与抽象交织的蒙太奇手法展现现代文明背后的精神荒原。钢筋森林的冰冷轮廓与霓虹灯牌的虚假温度形成强烈反差,街道上漂游的塑料袋成为人类存在过的唯一痕迹,这种物象选择暗喻着消费主义狂欢后的集体性失落。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褪色广告牌"与"生锈的自动贩卖机"构成双重隐喻,既指向物质文明的速朽本质,又暗示情感纽带的机械化溃败。电子雨滴的意象将数字时代的情感荒漠具象化,数据洪流中漂浮的残存记忆如同断电的显示屏,在意识深处闪烁最后的光斑。那座永不关闭的地铁站成为当代西西弗斯式的存在寓言,穿行其间的不是具象的乘客,而是被异化为时间零件的孤独灵魂。歌词刻意模糊了城市陷落的具体缘由,转而聚焦于废墟中滋长的微妙生机——裂缝里蔓生的野蔷薇与废弃影院中自我放映的胶片,这些倔强的生命迹象解构了绝对虚无,在解构中重建着关于救赎的隐秘叙事。全篇通过物质空间的衰败映射精神图景的坍缩,最终在末节转向星空与黎明的意象群,完成从赛博朋克式绝望到存在主义式觉醒的审美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