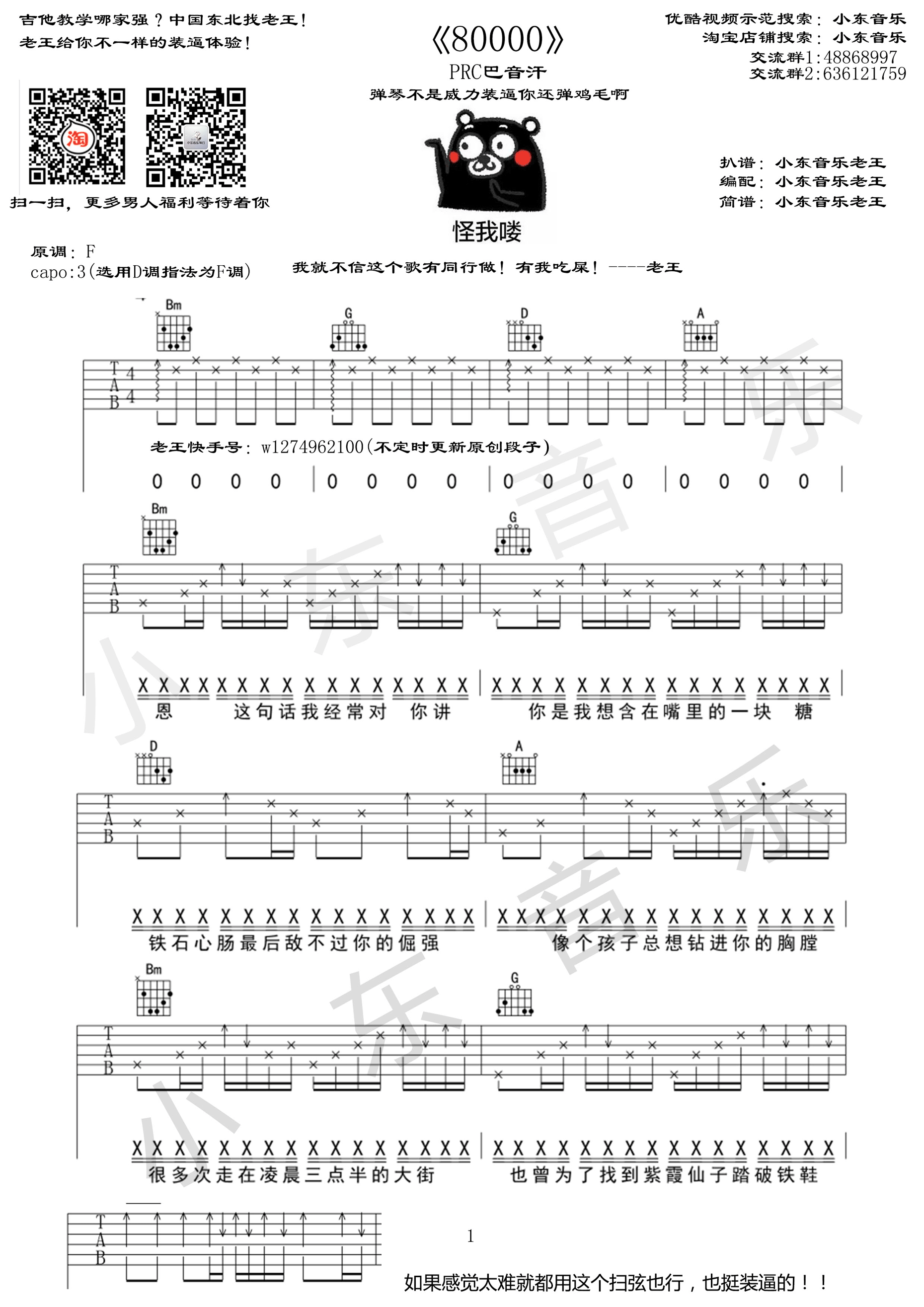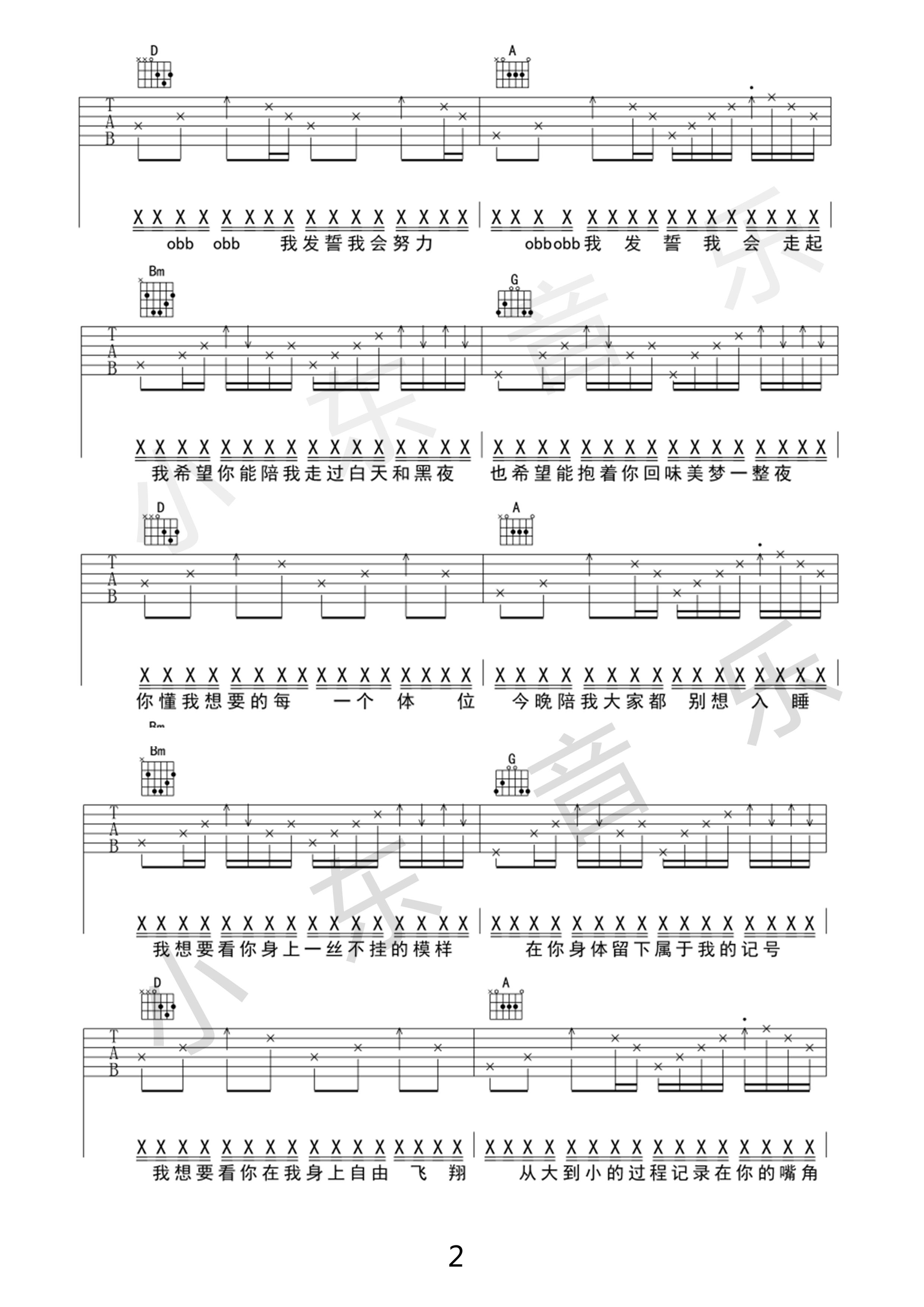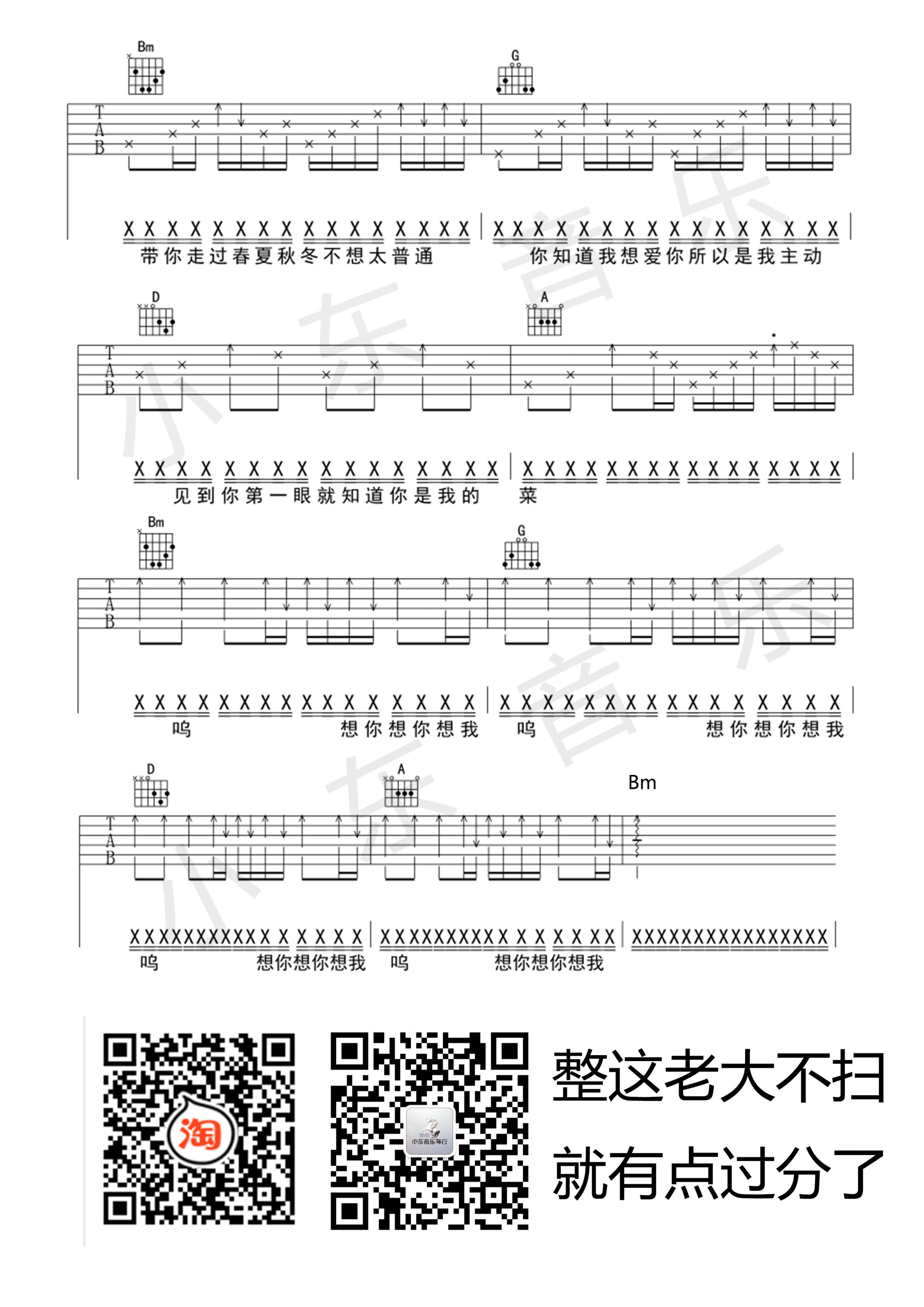《80000》以锋利的笔触解剖了当代都市青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惘,将物质欲望与灵魂空虚的尖锐矛盾具象化为数字时代的生存寓言。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数字意象构成冰冷的计量单位,丈量着被消费主义异化的生命价值——工资数额成为人格标尺,房租数字化作精神牢笼,社交媒体的点赞数异化为存在证明。这种数字化生存的荒诞性在电子合成器制造的机械节拍中形成听觉隐喻,如同被算法操控的提线木偶在数据迷宫中机械舞动。碎片化的意识流叙事手法拼贴出后现代生活的魔幻图景:便利店暖光与凌晨失眠的蓝光交替闪烁,信用卡账单与未读信息在手机锁屏上交叠,抒情主体在物质丰裕与精神赤贫的悖论中持续失语。歌词刻意保留的语法断裂与意义留白,恰似被信息洪流冲散的注意力,在物欲横流的都市夜景中,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当"80000"这个抽象数字成为全篇诗眼,其背后隐藏的已不仅是具体的经济压力,更是整个世代对存在意义的集体叩问——在价格标注一切的时代,灵魂究竟该如何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