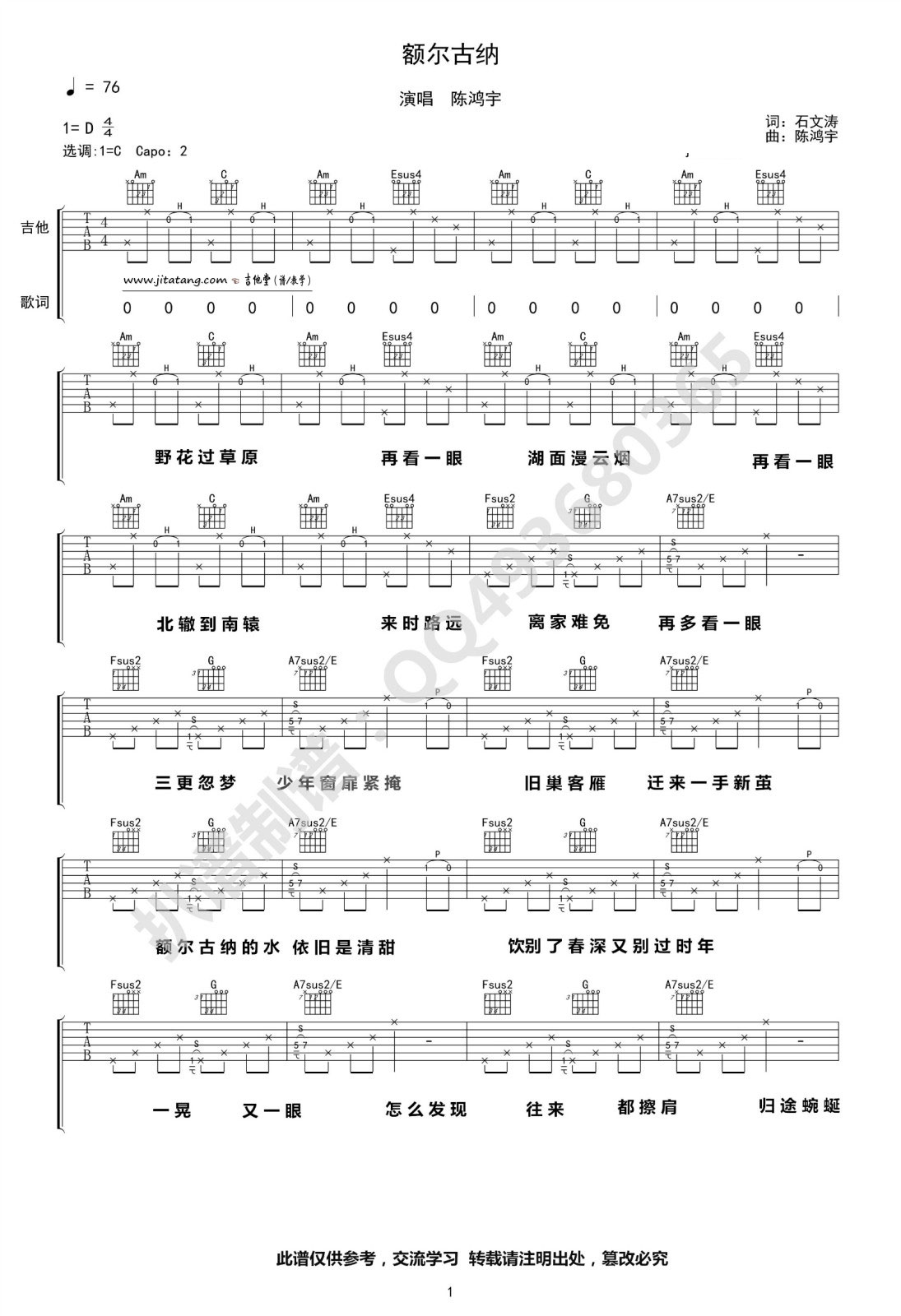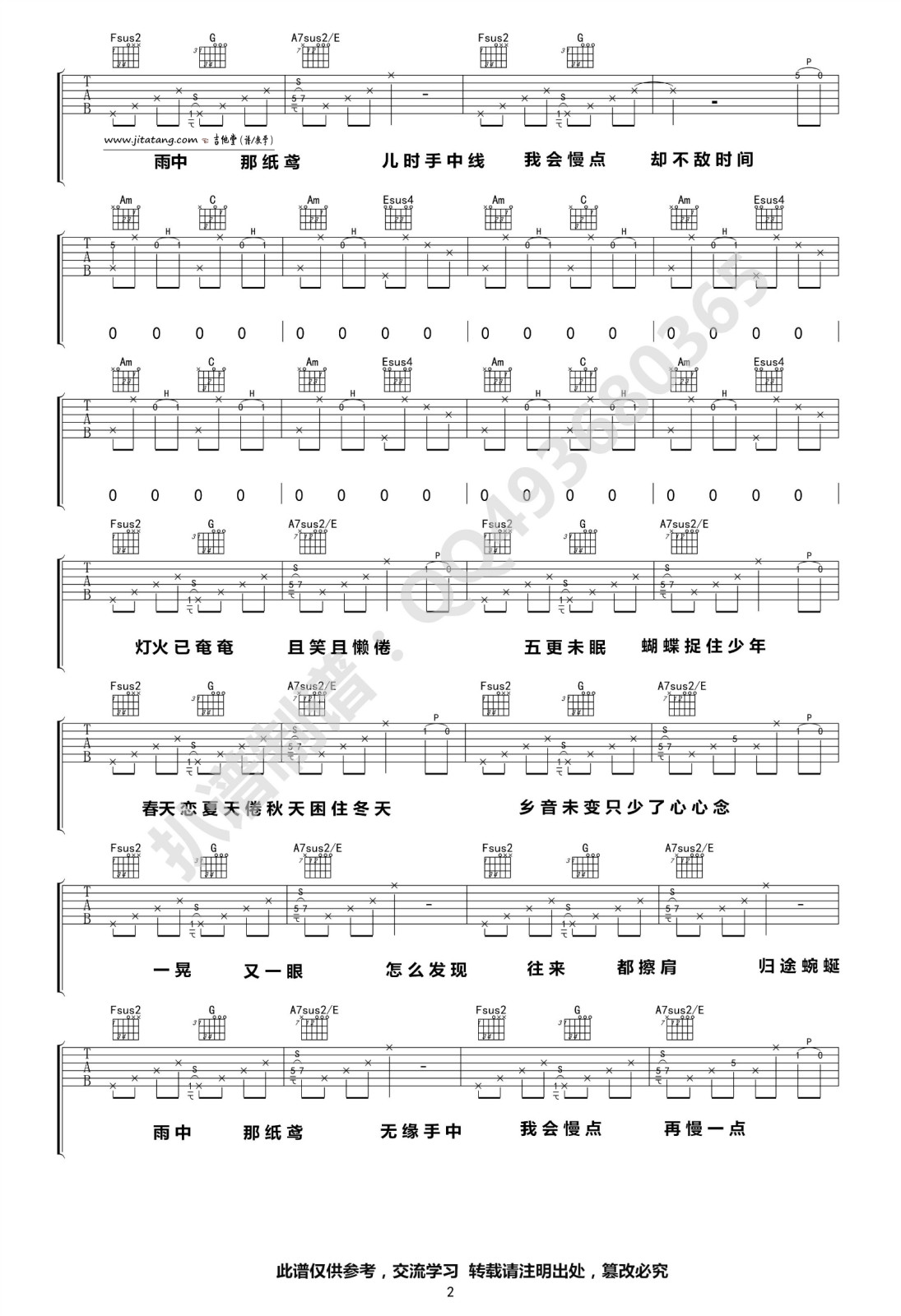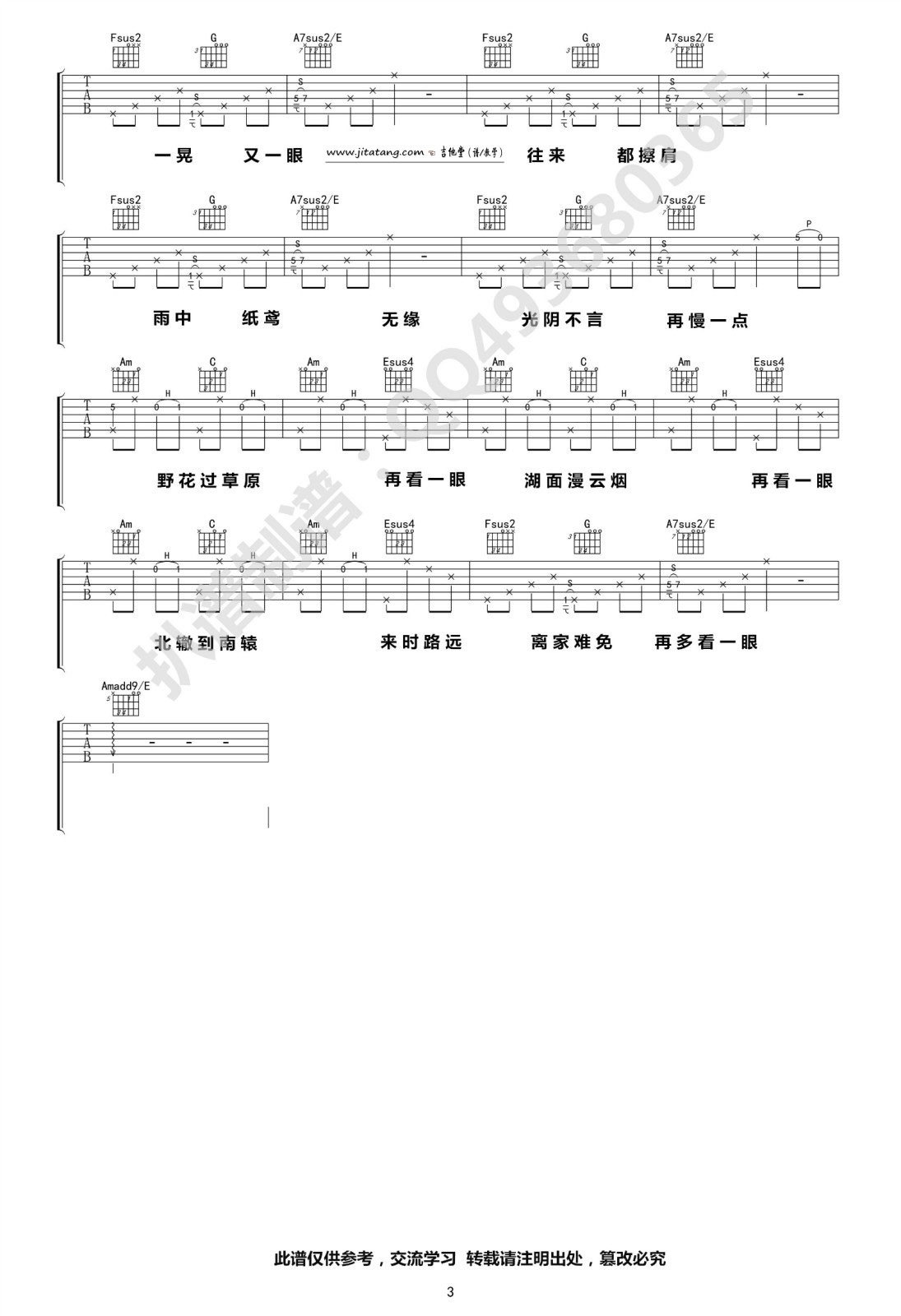《额尔古纳》以北方河流为意象载体,构建了一幅游牧文明与现代性交织的精神图谱。歌词中蜿蜒的河水不仅是地理坐标,更隐喻着时间长河里消逝的古老文明,马蹄印在冻土上刻写的不仅是迁徙路线,更是民族记忆的年轮。白桦林与驯鹿铃的意象群构成生态文明的图腾,而逐渐黯哑的萨满鼓声则暗示着传统信仰体系在现代语境中的式微。敖包石堆在月光下的投影被解构为文明碎片的象征,游牧民族的苍穹哲学与定居文明的钢筋秩序形成隐秘对话。风雪中的迁徙路线实为文化基因的传递路径,勒勒车辙里沉淀的不仅是草原尘埃,更有未被现代性完全收编的生存智慧。整首作品通过自然意象与人文符号的多重编码,完成对消逝文明的考古式书写,河流的永恒流动性与文明的阶段性断裂形成张力结构,最终在月夜篝火的集体记忆场景中达成诗意和解,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边缘文明的困境与尊严。这种表达既非简单的怀旧挽歌,也非进步主义的赞歌,而是试图在文化褶皱中寻找更具包容性的文明对话可能。